从五谷杂粮到植物根叶,通过烹饪技艺化“不可能”为美味,既减少浪费,又保障营养。这是中国饮食传统强调对食材的极致利用,是源于历史上应对饥荒的饮食智慧,更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东方膳食的深层价值,在于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了全球性挑战:如何以有限资源滋养更多人口,同时减少生态压力?答案或许就藏在“一粥一饭”的千年智慧中——珍惜食物,顺应自然,方能行稳致远。
祖籍重庆的周教授,他的饮食认知始终带着地域文化碰撞的印记。重庆,这座被称作“中国火锅之都”的城市,满是浓郁的烟火气。重庆及云贵川一带的人,对食材的利用、味觉层次的追求有着天然的执着,这种“江湖气”的饮食文化,早早融入他的成长轨迹。更深刻的影响来自家庭教育:他的父母亲历过中国苦难的饥荒岁月,深知“有饭吃”是生存的底线,因此从小就要求他“上手做饭”,“你一定要会自己做饭吃”这句话,不仅是生活技能的传授,更是对饥饿记忆的警醒。在这样的环境里,周教授练就了做家常菜的本领,他烧的菜虽非大厨级别的精致,却带着重庆饮食特有的“爽利”口感,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
1从重庆的烟火气到杭州的清淡饮食
后来,他长期在杭州工作、学习与生活,这座江南城市的饮食风格与重庆形成鲜明反差——杭州饮食偏向健康清淡,更注重食材本味的呈现。初到杭州时,他经历了一段饮食文化的冲突与适应:一边是重庆饮食的重味鲜香,一边是江南饮食的清雅淡爽。但这份适应并未让他丢弃重庆饮食的底色,反而让他在两种风格的碰撞中,更直观地体会到中国饮食“因地制宜”的智慧——重庆的重味是对潮湿气候的适应,杭州的清淡是对江南物产的尊重,二者都是中国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鲜活注脚。如今的他,既能做出带着家乡烟火气的家常菜,也能欣赏江南饮食的雅致,成为地域饮食文化融合的亲历者。
东方膳食的两面性
《救荒本草》的饥荒智慧到扬名海外为中餐正名的扬名海外为中餐正名的《中国食谱》
周教授研究发现在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始终贯穿着“生存”与“尊严”两条主线,《救荒本草》与《中国食谱》便是这两条主线的典型载体,分别承载着古人应对饥荒的智慧与现代人为中餐正名的努力。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自然灾害频发、战乱不断,饥荒成为百姓生存的最大威胁。为帮助百姓自救,历届政府都会出版《救荒本草》——这类典籍并非单纯的医药著作,而是兼具“生存指南”与“饮食手册”的功能。书中详细记载了各类植物性原料的食用方法,哪怕是竹叶子、竹子花这类看似“无用”的食材,甚至是带有苦涩味、微毒的植物,都被纳入可食用范围。更关键的是,书中还传授了通过烹饪消解有害物质的技法:比如通过长时间煮制,去除植物中的苦涩味与毒性,将“不可食”转化为“可食”。周教授提到,在极端饥荒年代,中国人甚至会依据《救荒本草》,用树叶子揉搓取汁制成“观音豆腐”,或是食用竹花续命,这些技法既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绝境中求生的智慧。
如果说《救荒本草》是“活下去”的智慧,那么杨步伟女士所著的《中华食谱》,则是“活得有尊严”的宣言。近代以来,西方在殖民话语影响下,对中餐多有污名化——将中国人食用鸡爪、内脏等行为污蔑为“野蛮”,却忽视背后“物尽其用”的生存逻辑。而《中国食谱》直面这种误解,明确指出中餐的健康与营养属性:中餐从不刻意追求珍稀食材,而是秉持“杂食”理念,选取广泛的动植物原料,通过“快炒”(即西方认知中的“chop suey”)等简易烹饪技法,将多种食材混合烹制。这种方式不仅经济实惠、能快速果腹,更符合现代营养学“多元饮食”的原则,避免单一肉食导致的营养失衡,让普通百姓也能通过日常饮食获取均衡营养。
中餐的价值早已通过文化交流影响世界:唐代以后,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外销,以洁净、耐高温的特性,替代了欧洲传统的木器、陶器,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器皿与进食方式;茶叶经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播至南亚、东南亚,印度、印尼等地的茶种与种茶技术均源自中国,逐渐发展为当地重要产业;如今,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更援助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帮助当地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这些案例,都印证了中餐及其衍生智慧的全球价值,也让《中国食谱》的“正名”更具说服力。
2物尽其用的背后历经饥荒的中国人
“物尽其用”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核心关键词,但其背后并非刻意的“节约倡导”,而是无数中国人在漫长饥荒史中沉淀的生存本能。周教授坦言,中国历史上的“饥荒”并非偶然,而是常态——人口众多、黄河等水系频繁泛滥、战乱不断,再加上粮食分配不均(权贵阶层占据大量资源,百姓需缴纳重税支援中央,即便富庶的江南也需通过漕运向北方输送粮食),让“饿肚子”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记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浪费任何可食用食材”成为百姓的生存选择。对于动物性食材,中国人不仅食用鸡胸、鱼肉等“主流部位”,更会将鸡爪、内脏、头部等“边角料”充分利用:通过卤制、红烧等技法,让鸡爪成为美味;通过爆炒、炖煮,让内脏变得鲜香。对于植物性食材,更是极尽所能——从《救荒本草》中记载的竹叶子、竹花,到江南地区的“水八仙”水生植物,再到通过揉搓取汁制成的观音豆腐,甚至是带有苦涩味的野菜,都能通过焯水、腌制等技法转化为可食用的食物。周教授提到,他的父母之所以从小要求孩子学做饭,正是因为亲历过“没东西吃”的日子,深知“获取食物、制作食物”是生存的基本技能,这种记忆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饮食基因”。
这种“物尽其用”的理念,还体现在海外华人的生存智慧中。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大量华人前往北美淘金、南洋谋生,“菜刀”成为他们的生存工具之一——通过开设中餐馆,用“物尽其用”的烹饪技法制作经济实惠的饭菜,不仅养活了自己,更让中餐获得当地族群的认可。对比西方因殖民财富积累形成的“饮食浪费”(如只取鱼肉部分、丢弃内脏,因“心理膈应”拒绝食用鸡爪等),中国人的“物尽其用”更像是对食物的敬畏:食物不是“可随意丢弃的商品”,而是“活命的根本”,这种认知即便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今天仍未褪色,“反食物浪费法”的推行、“光盘行动”的倡导,正是对这种传统的延续。

3可持续健康饮食的指引东方膳食
如今,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与健康挑战,而中国的东方膳食文化,恰好为“可持续健康饮食”提供了清晰指引。这种指引植根于中国传统饮食理念与实践,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东方膳食的核心,是“平衡”与“适度”。《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畜为益”,强调以植物性饮食(五谷)为基础,动物性饮食(五畜)为补充,这种结构既符合“物尽其用”的逻辑,也契合现代营养学“多元摄入”的原则。周鸿承指出,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中,植物性食材占比极高——无论是江南的时蔬、西南的野菜,还是北方的杂粮,都能通过腌制、发酵、快炒等多样化烹饪技法成为美味。这种饮食结构不仅能避免单一肉食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还能减少对环境的负担(动物性养殖的碳排放远高于植物种植)。
同时,东方膳食的“可持续”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古代的《救荒本草》教会百姓利用有限资源求生,现代的“大食物观”则倡导“向森林要食物、向海洋要食物、向沙漠要食物”——从沙漠中的沙棘果汁,到青藏高原的青稞、牦牛肉,再到海洋中的各类水产品,中国人始终在探索“充分利用自然馈赠”的路径。这种实践与西方“为追求口感浪费食材”的饮食观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社会因经济发达,常因“心理偏好”丢弃可食用的食材,却忽视全球仍有大量人口面临饥饿;而中国的东方膳食,用“物尽其用”的实践,践行着“节约粮食、应对危机”的全球责任。
更重要的是,东方膳食打破了“健康饮食是富人特权”的误区。在西方,健康饮食常与“高价有机食材”“精致素食餐厅”绑定,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而在中国,健康饮食就是日常——一把青菜、一碗杂粮饭、一份快炒时蔬,成本低廉却营养均衡。周鸿承提到,中国的植物性食材丰富且价格亲民,普通家庭无需高额支出,就能通过“五谷+蔬菜+少量肉食”的搭配,实现健康饮食,这种“普惠性”让东方膳食成为适合全球大众的饮食方案。
在采访的最后,周教授期待良食大会能成为“加速者”:一方面,趁着中餐申报人类非遗的契机,放大“物尽其用”“五味调和”等东方饮食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契合点,通过具体案例(如观音豆腐的制作、食材的物尽其用),让全球更直观地理解东方膳食的智慧;另一方面,推动东西方健康膳食对话走向平等,帮助东方膳食在全球食物流动与健康餐桌议题中获得更多尊重与认可,让中国的饮食智慧能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构建健康饮食体系提供切实参考,真正实现“用东方方案助力全球饮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注:良食基金采访报道,2025年10月6日,发表在“何以为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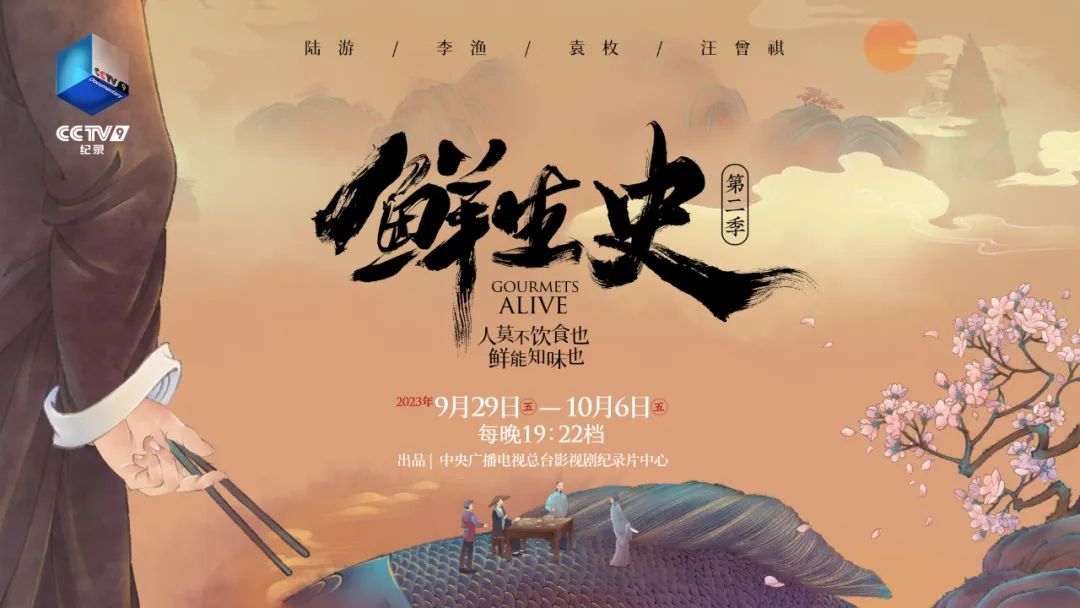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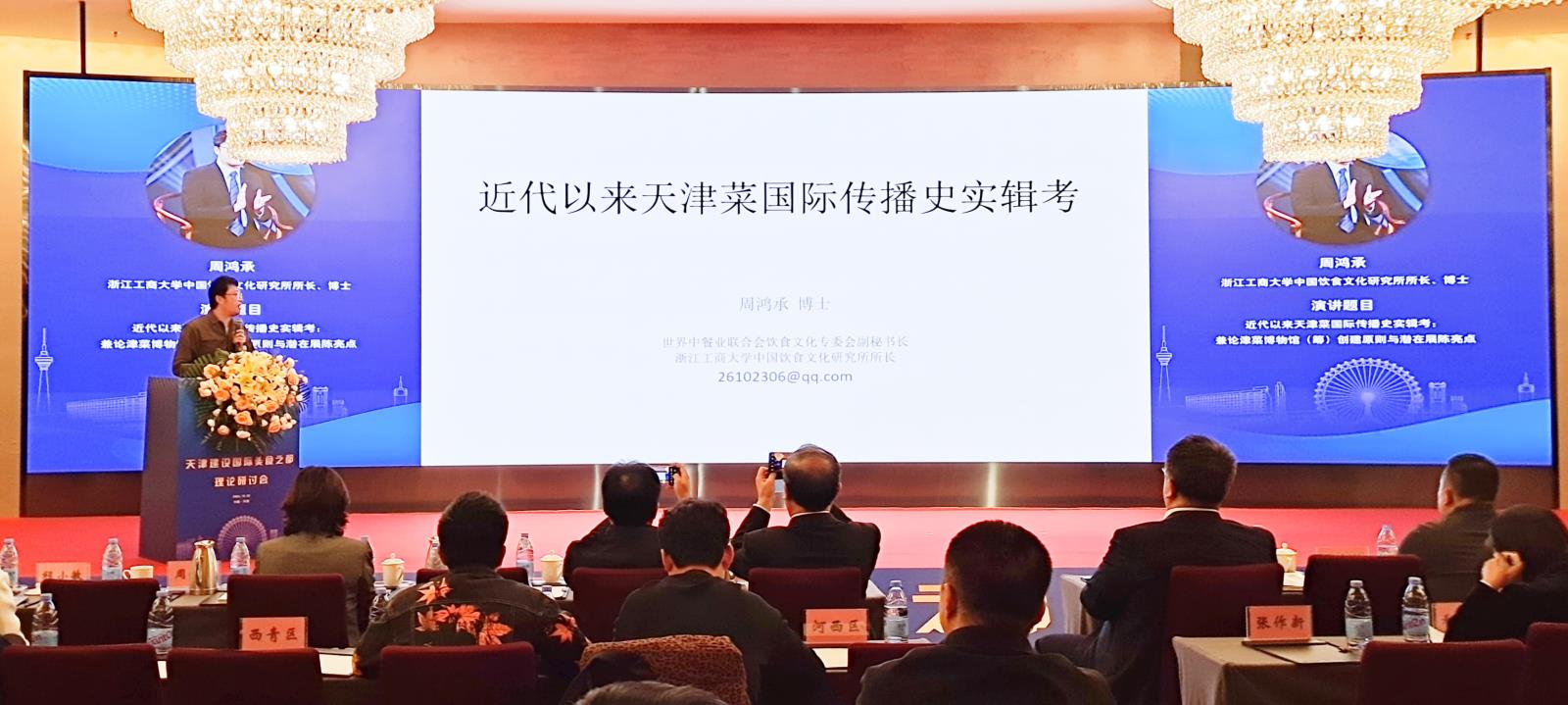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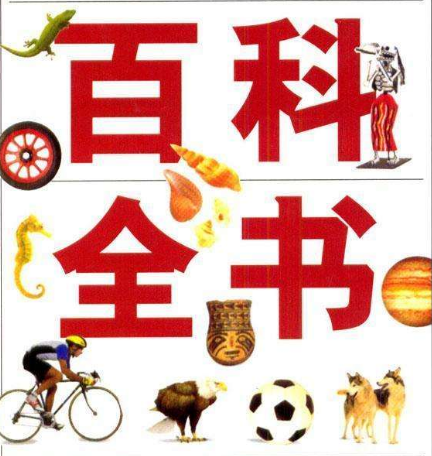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