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中国饮食文化遗产研究的探索与创新
赵荣光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的周鸿承博士,致力于饮食史、中外交流领域研究已逾十年,传统与非遗价值食事研究是他一向关注的选项。他的《杭州饮食文化遗产研究》一书是我主理的“杭州食事研究丛书”之一,付梓之际请我为序。借周鸿承博士《杭州饮食文化遗产研究》出版之机说点相关的话,理所当然,义不容辞。
应当说,具有非遗价值的食事研究选项和强烈的再现与承传意识,是我饮食史、饮食文化与食学研究伊始的明确原则、鲜明特色。我依据万卷《衍圣公府档案》、两亿字现存《清宫御茶膳房档案》,以及不可胜计卷帙历代官私史乘、典献文存、食书披览,数十年田野考察、场景再现、模拟实验的许多研究都秉持这一原则,具有这一性质。国家级非遗目录的“孔府菜”依据的就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衍圣公府档案》、明清食书历史场景再现研究的结果,曲阜的“汉代官场宴会仪礼”非遗名录则是我在第五届亚洲食学论坛上展示的恢复性研究成果。至于我的“廿四节令食俗与食品文化”恢复性研究不仅成了各级非遗名录,而且也成了餐饮业经营的热销亮点。可以说,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对中国食事领域的非遗问题,我们不仅最具发言权,而且也有较丰富的经验。
自2010年法国传统美食及墨西哥传统美食成功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以来,土耳其小麦粥、地中海美食、日本和食、韩国腌制越冬泡菜等美食项目先后成功申请成为世界非遗项目。这些无疑一再冲击餐饮业界的“中国烹饪”申遗热情,一再激起回响。在“中国烹饪”申遗转换为“中华食事文化非遗”承传认识之前,“中国烹饪申遗”的主事者还会经相当时间的痛苦思虑。始则踌躇满志,继而惊慌失措,随即仓促应对,这种满清帝国末期热议、侈谈洋务的情态让我们忧虑。
食事遗产无疑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文化财之一。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饮食文化遗产的普查、研究和保护,必须首先是作为本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实践的基本内容之一,然后才是面向世界的民族文化传播与展示。
我和季鸿崑先生都曾在多年前撰文探讨过中国饮食类文化遗产的类型和品种,保护原则与措施。我们对国内食事遗产“重噱头、轻研究”、“重申报、轻保护”的社会现象也曾发表过批评意见。2015年曲阜第五届亚洲食学论坛上,我和数十位食学专家共同呼吁有关部门考虑将“衍圣公府食事”作为中华民族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向教科文组织申遗。这一呼吁受到新华网、中华文物网等媒体的宣传报道,社会反响强烈。应当说,我国饮食文化遗产的理论探讨、保护实践情态严峻,需要认真严肃面对的问题还有许多。
当前,国内非遗管理部分划分的十大类型中并无饮食类文化遗产,这对于包括饮食在内的其他专门性强、分布广、数量大的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显然不利。国内文化遗产学、历史学、饮食文化学界尚无针对中国饮食文化遗产概念梳理、历史理论、类型解析、价值评估、管理方法、保存活化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专著。周鸿承博士以古都杭州为个案,从区域性视角探讨中国城市饮食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杭州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积极探索现有管理模式下,如何使地方饮食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开发建设“各取所需”,这样的研究探讨有助于提高我国饮食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周博士将杭州饮食文化遗产分为食材类饮食文化遗产、技艺类饮食文化遗产、器具类饮食文化遗产、民俗类饮食文化遗产、文献类饮食文化遗产五大类型,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有效总结,也是理论认知上的提升。这种创新性的分类方法对国内非遗“十大类”划分标准来说,应当具有理论探讨和实践参照的积极意义。该书特别以中国杭帮菜博物馆为例,探讨了后遗产时代饮食博物馆在地方饮食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管理实践领域的功能和价值。书中对国内外饮食博物馆的数量、分布和类型等统计数据新颖、分析扎实。具有非遗性质食事中的传统食品制作与消费,因为是即时性消费文化,其“与时俱进”的演变是必然的规律,其承传原则只能是双重标准、两条道路:即博物馆与市场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因此,《杭州饮食文化遗产研究》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在未来深化研究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文化遗产的概念中,是否仅有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以良渚农业遗址为例,这种物质性的农业遗产中,饮食文化遗产是不是其农业文明的核心?也就是说,遗址类的物质性饮食文化遗产是否在中国具有普遍性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另外,有关杭州下属村镇的饮食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田野调查、实地走访、座谈访问等工作还需要强化。人们习惯说:“地方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的,在科技不断改变旧生态和旧我的时潮中,证明和坚守不可或缺的自我是学者和文化人不容稍殆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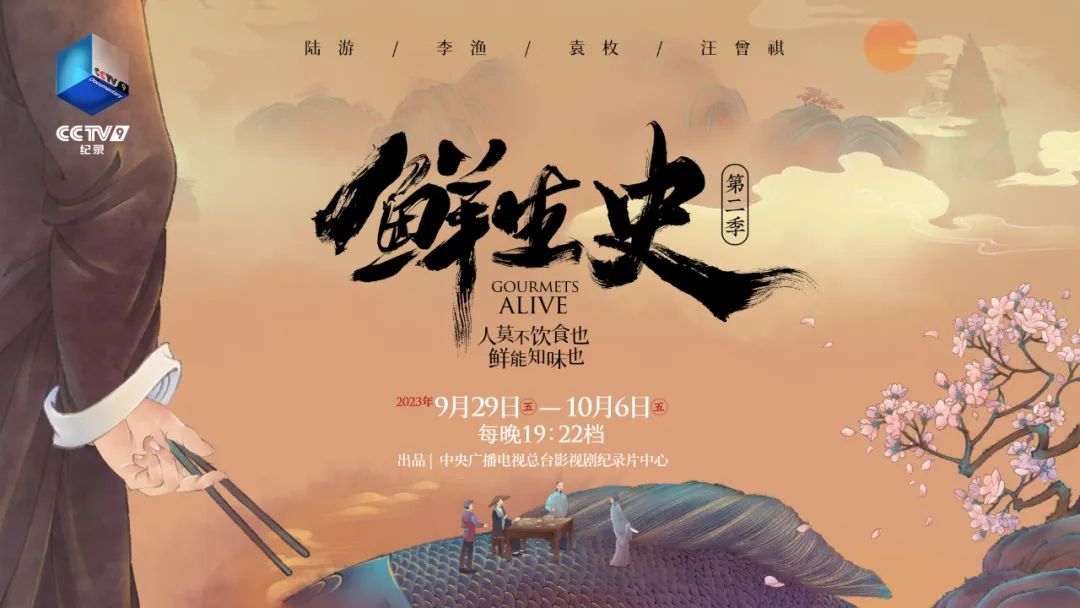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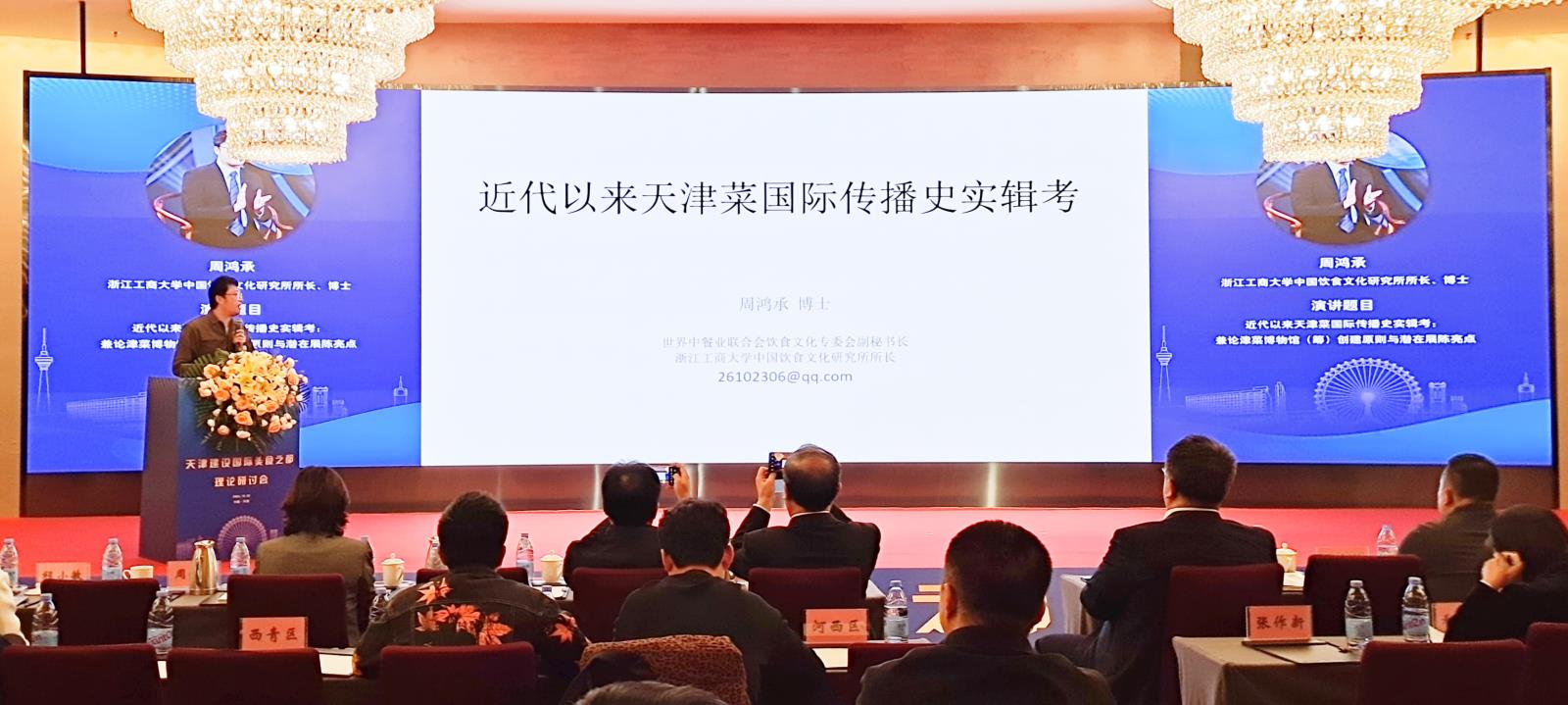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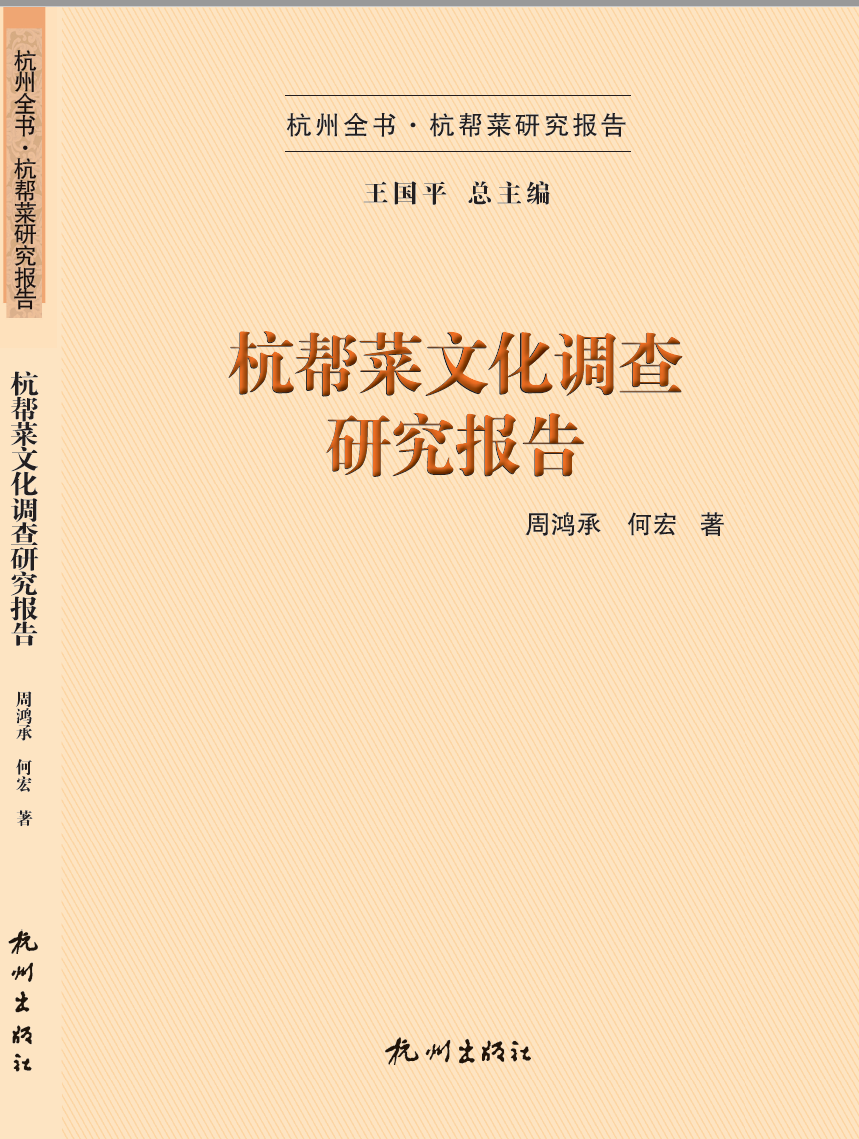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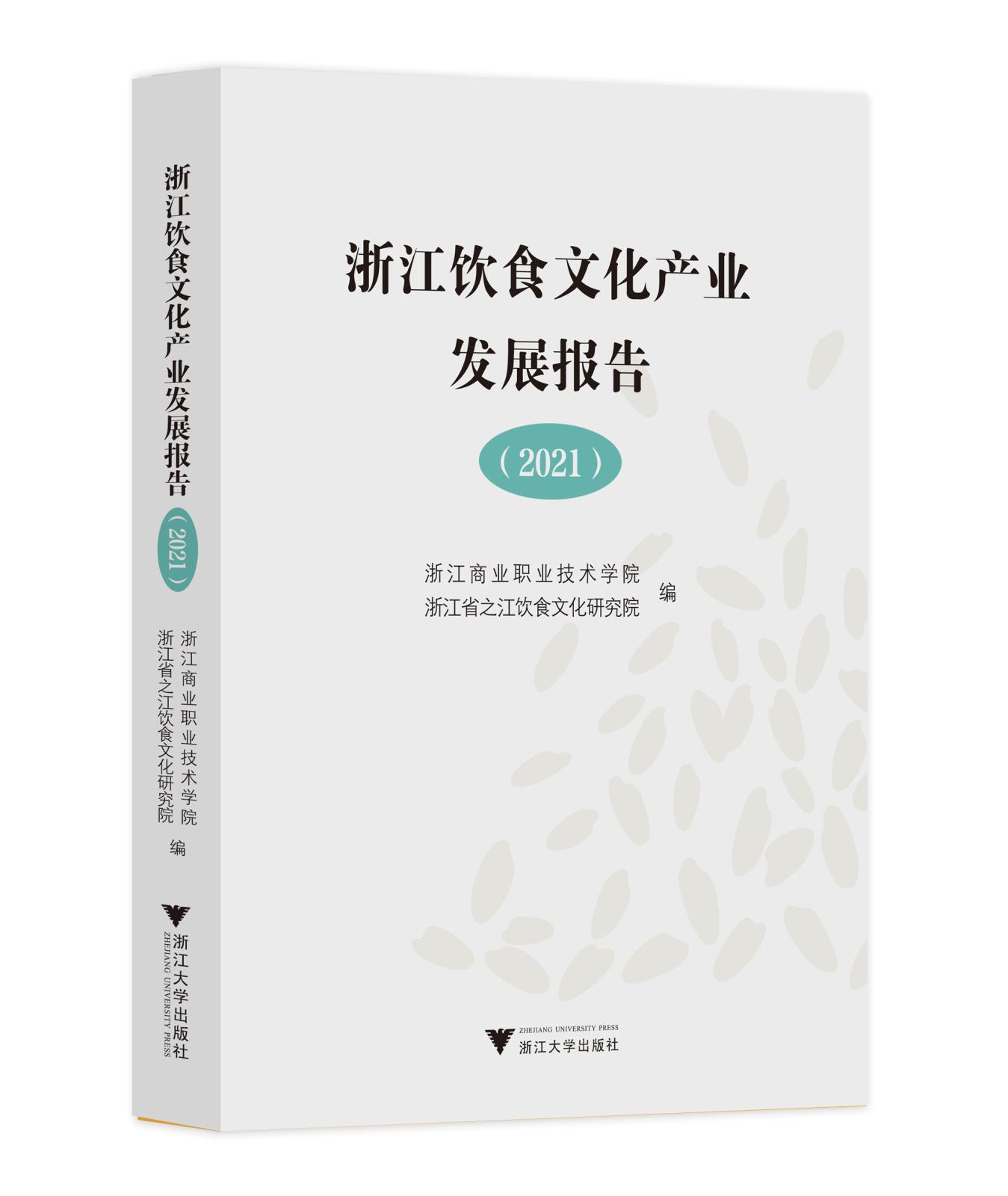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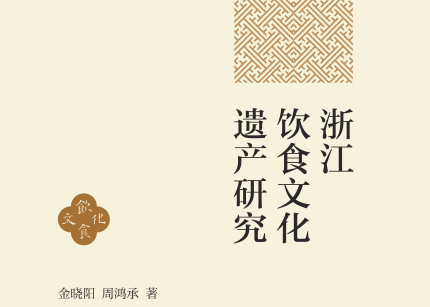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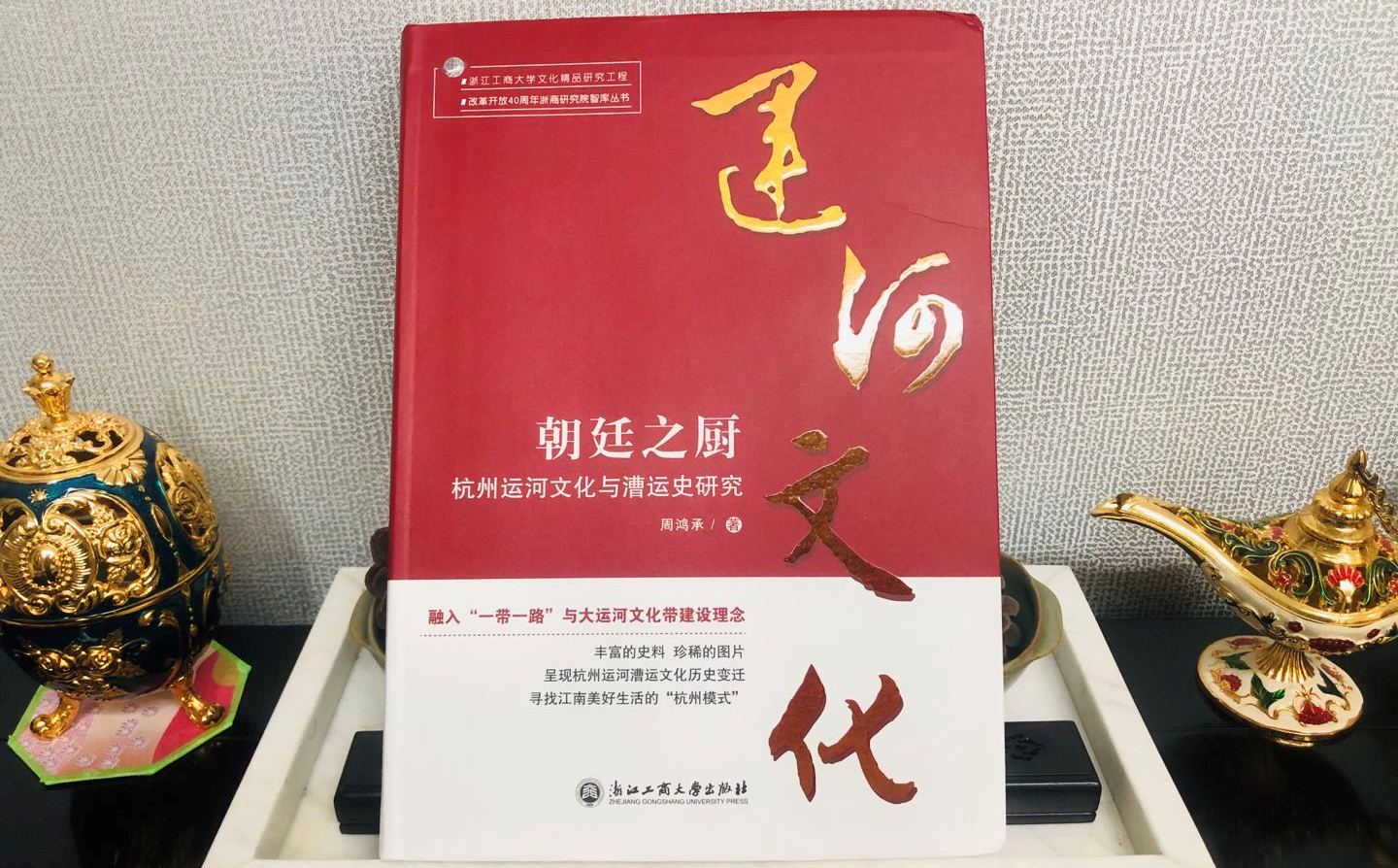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